解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:“千万工程”不是造点
近日,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,文件名为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。笔者根据浙江省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(以下简称“千万工程”)的调查,以及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,做个人化解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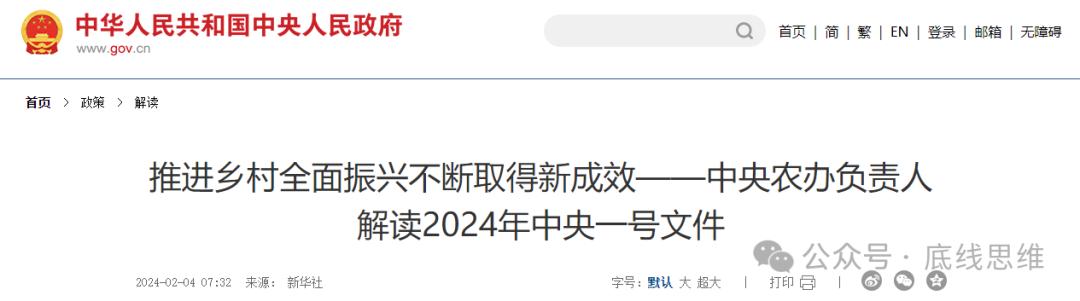
1.目标与方法
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,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目标。“千万工程”则是浙江持续坚持20年的时间经验,是乡村振兴的方法路径。目标和方法之间,有一定的辩证关系,我们需要仔细辨析。
一是防止用方法替代目标。
典型示范是我们党抓工作的重要方法,通过典型示范,总结普遍性的工作方法,从而实现以点带面。但我们的调研发现,很多地方在进行乡村振兴示范时,存在目标替代的做法,人为拔高示范点标准,过度包装和总结其经验,这是违背“千万工程”的基本经验的。
不少地方在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,似乎都有了路径依赖,希望通过某个具有现实度的示范点来体现自己的工作成绩。因此,往往是抓了若干个点,却忘记了全面。有些示范点,从新农村建设、美丽乡村建设开始,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,都不知道投入了多少钱,示范了多少年,结果还是没有示范效果,连隔壁村都没有示范带动起来。这种以点代面的工作方法,我们要警惕。
千万要警惕,别把“千万工程”学习成造点的工程。
二是防止用特殊代替一般。
文件也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,分类推进。关键是,地方特点和类别怎么操作呢?我们认为,最好的划分标准是城乡关系。无论是乡村振兴,还是千万工程,都是在特定的城乡关系中开展的。
浙江“千万工程”的发生背景是,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,大多数农村地区也被纳入了城市带。城镇化工业化造成了村庄环境污染等问题,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资金和资源条件率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,通过千万工程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,是有合理性的。
现如今,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关系,其实和浙江是完全不同的。如果说浙江农村属于城市,那么,普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属于农村。换言之,“以城带乡、以工补农”在很多中西部地区是很难实施的。
从我们的调查看,很多中西部地区去浙江学习,都重视学习具体的经验模式,如某个示范点的乡村建设、乡村发展和乡村运营的经验,最后发现,其实没有办法学。他们往往是满怀期待而去,满怀失望而归。
其中的原因是,浙江不少明星村,几乎都有意识地总结了一套经验模式,这些模式的特点都是无比高大上,用特殊代替一般,这些浙江的示范点在浙江内部都难以通融,何况是到浙江之外的地区?
因此,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,重要的是学习方法,而不是具体模式。这些方法,无非是结合地方的资源条件和区位特征,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方法,千万别拔高,要立足长远,久久为功。

百亿花园村成为乡村振兴样板(图/新华社)
2.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
一号文件专门用一章来讲粮食安全问题。从我们的调查来看,自上而下都很重视粮食安全,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粮食安全。但在实践中,有些基层反应突出的问题,需要引起高度重视。
一是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理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。
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理,关系到粮食安全的基础要素——土地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从实践看,非农化和非粮化的土地,有极其复杂的制度和历史原因。
在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,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,更是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基础,地方政府有冲动把土地非农化。其结果是,好地盖房子去了,差地甚至不适合耕种的土地,反而成了基本农田。在工业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,在增减挂钩等政策诱导下,也有强烈冲动通过增加耕地指标,通过交易获取财政收入,客观上也导致了一些耕地质量不高,甚至因此而影响了生态。
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,地方政府的农村工作的重心是农民增收,想方设法鼓励和引导农民多元化农业生产,鼓励种植经济作物,甚至默许农民在农地上发展养殖业等附加值更高的产业。在一些地区,地方政府通过“逼民致富”,的确发展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,造福了农民。但客观上,发达的农业特色产业,往往也意味着土地的非粮化问题。
因此,一刀切的问题实质是,将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唯一且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,传导给了基层政府。这迫使基层政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,出现了折腾群众、不切实际的做法。
早期的“千万工程”的可贵经验其实是切合农村实际,以群众利益为导向的。比如,村庄整治会充分考虑到群众出行需要,该修路修路,该架桥架桥。但当前在严苛土地管制下,基层根本就不可能根据实际来更加高效地运用土地,到处都是红线,基层基本上没有“有力有效”推行乡村振兴的空间了。
二是农业经营模式问题。
近些年来农业经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:一方面,农业生产力发生了巨变,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农技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;另一方面,农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变,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,农业经营主体也多元化,种田大户所占比例越来越高。
在长三角等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,本地小农几乎都不种田了,转而依靠种田大户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,也有意通过补贴、鼓励土地流转等方式,引入种田大户。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结果,种田大户似乎是为政府种田,农业经营者并没有种什么的自由,完全听命于政府,其农业生产效率其实非常低。
而在一些粮食主产区,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多少补贴,且很多种田大户还要想方设法多种地,如通过社会化服务的方式,将小农排斥在外,小农种地越来越难。但麻烦的是,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需要以农为生的农民,他们一旦没有充分就业,就很可能对种田大户产生意见。客观上,去年一些地区出现的“抢大户”现象,是一个警示。
一号文件专门强调小农经营为主,这符合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农业经营现实。某种意义上,小农指的是没办法脱离土地的最弱势的农民,保障他们的劳作权,不仅是一个农业问题,还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当前,各地已经在试点土地二轮延包政策,这不仅涉及到粮食安全,更涉及到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农村稳定,需要慎之又慎。
三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。
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5年衔接期已经过去了三年,在一些地区,脱贫监测仍然是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,但也给基层造成了极大困扰。其核心问题是,脱贫监测的系统极其不接地气,但凡群众上学、就医等,就要填表,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,造成了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。
比如,某些地区的主管部门人为规定脱贫户的有一定比例的收入增长率,而2023年又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,农民增收(包括脱贫户增收)压力极大的时候,这给扶贫干部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很多基层干部调侃,不少地方基层干部的收入都下调了,结果贫困监测户的收入却有了较大比例的增长,说出去都是笑话。
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让脱贫监测和最低保障制度相衔接,我们认为,要尽早并轨,低保政策又较为完善的执行系统,用低保制度代替脱贫监测就行了。并且,服务于脱贫攻坚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,也要尽快优化,给派驻单位减压,也给基层党组织有更大的自主空间。

图为綦江区千秋村贫困户肖礼树喜迁新居(图/脱贫攻坚网络展)
3.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
“千万工程”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建设经验,具体而言是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切入点的不断升级迭代的经验。当前,各地在推行乡村振兴工作中,也主要是从人居环境治理切入的。从我们的调研来看,有几个方面需要重视。
一是人居环境治理是最有显示度的工作,但未必是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工作。
这意味着,地方政府的工作和农民需求之间,其实是不匹配的。在不少地方,人居环境治理出现了政府在动、群众在看的现象。比如,在厕所革命过程中,很多地方的按指标推进,时间紧、任务重,且好高骛远,工程质量完全无法保障,最后出现了浪费。
哪怕是在浙江地区,有些地方的农村污水管网仍然是没办法保证质量的,根本就没有基础设施,也没有足够的运营经费来有效处理污水。基层干部群众反映,这种无法正常使用的污水处理管网,还不如以前的农户分散处理来得环保。
很多地方在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,急于求成,出现了越俎代庖,增加基层负担的现象。现如今,人居环境治理成了很多中西部地区乡村两级的财政负担,有些村庄因此欠下了村级债务,有些乡镇因此陷入保运转的困境。这两年基层“三保”的压力比较大,有基层领导反映,其中的一个压力源就是人居环境治理。
我们认为,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量力而行,也要适应群众的诉求,完全没必要好高骛远。群众有需要,政府需要回应;群众没有需要,就要缓一缓,不要替群众着急。有些地方为了人居环境治理,要求群众不养猪,要把鸡鸭圈养起来,这都让人哭笑不得。乡村建设一方面要把农村建得像农村,有土猪土鸡吃,但另一方面又不让农民养,这是为了干啥呢?
二是乡村治理要重提群众路线和村民自治。
这些年,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,但悖论是,乡村治理体系是健全了,但乡村治理能力却下降了。现如今,不少地方哪怕是让群众来开个会,都要给群众发钱。基层干部天天忙得要死,却见不了群众,群众的诉求也没办法有效回应。农村的这种治理状况,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。
如果不动员群众,或者是依靠利益俘获来假动员群众,乡村治理就不可能有力量。应该清楚的是,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与群众动员之间,是一体两面。如果党组织不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越是加强党组织建设,就越是可能把党员和党组织封闭起来,成了一个利益集团。基层干部真把自己当成干部,并不是什么好事。
如果不以自治为准则,则德治和法治也是无从谈起的。近年来,各地经常出现基层干部“好心办坏事”的情况,比如,在移风易俗过程中侵害群众权益。其中的原因,无非是基层干部已经无法通过村民自治的办法,依靠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了。而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,越来越依赖于上级的政策,越来越依赖于行政措施,群众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等,越来越不起效果了。
当群众内部没有共识,而党组织又不和群众在一起时,乡村治理只会越来越臃肿,越来越没有效率。

